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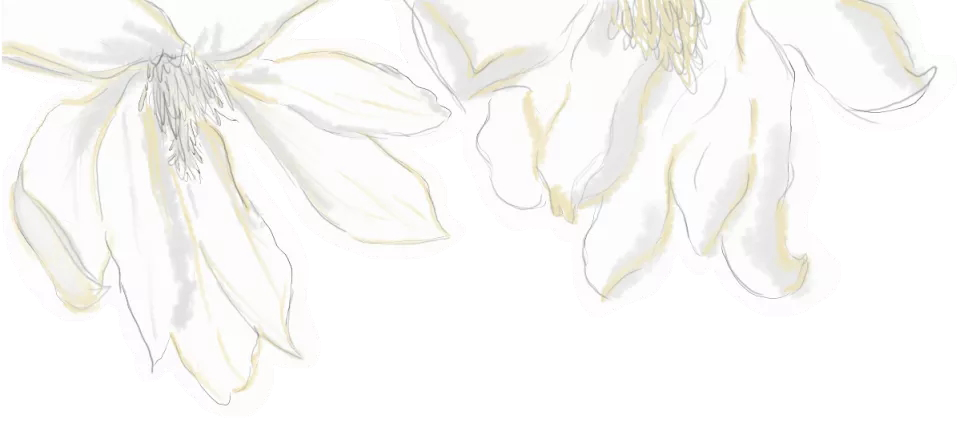

孙老太太

作者:于树刚

孙老太太是我儿时认的一位干娘。因为我在家中排行最小,拿俺当地土语讲:是老疙瘩,老邦子。体格不看强,柔弱。如同一根藤上结的那瓜,是末稍上的“秋纽子”。
我们当地有一种风俗:为了使这样的孩子好养活,一般要去庙宇,道观“记名”。或是起个狗啊,猫啊----的小名,或找个行善人家去认个干亲。可我小时候经过土地改革打封建及抗美援朝战事等,小镇有名的万发宫(即当地老人说的大庙或娘娘庙)早已废了,被部队占了,后来交地方,为现在的解放小学地点。卧虎山上理教的东西公所,一变成了结核病院,一变成了农业学校。家人只好给我认干亲,选了几家,选中了街斜对面的孙老太太。干娘孙老太太那时就好60岁的人了。那年月人显老,60岁的人就老态龙钟了:花白的头发,清瘦。小脚,但干净利索。常年穿一套大襟青布衫。她心眼好轧乎人。开朗,崇尚进步,她老头死于公务,政府给一定的待遇。抗美援朝,她亲送独子上了前线,一时街坊邻里传为佳话。
她的儿媳那时还没有孩子,清手利脚。在她的支持下参加了农会,可不知咋搞的竟移情别恋,提出离婚另嫁,闹到法院,孙老太太胜诉:说是现役军人还在前线,不准离婚。后来收斂,孙老太太大度,婆媳和好如初。不过每当干娘对我痛爱有加时,她总用白眼看我,自小我就怕她。
干娘住的房子虽是临街,但特别窄:一间房外,有一个过道通后院,一间屋里一铺火炕一张桌子一个凳,一张儿子参军出国前与母亲媳妇照的相片,挂在墙中央。桌子上有一座钟,上盖一小红布:说是土改时分的胜利果实。
干娘孙老太太,常年手握一个铜水烟袋。我每天的任务之一:就是给她装烟,每每是打开那圆形的小盖将黄色的烟末装入烟仓,看她慢慢地吸,听着水烟袋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着,伴着那轻袅的烟雾,这时半眯着眼的干娘,仿佛是一尊入定的菩萨。我第二个任务就是每天搬那木凳到大门外爬上去,在她的监督下,擦那挂在门框上方的长方形《军属光荣》的牌子,一天一次风雨不误。
干娘特别痛爱我,倚门倚闾,我一旦几日未去,干娘就想的了不得。有啥好吃的总留些给我。平时不准我乱跑,常让我坐在她的炕上,和她玩拧铜大钱猜字镘的游戏。可多数是听她讲“呱”,她讲的那些故事,不像《聊斋志异》中都是狐狸精,花精一类的。大都是日常生活中鸡鸭鹅狗的事,至今记忆最深的是:老鼠娶亲的故事。说是每年的正月初十是老鼠娶亲嫁女的日子,晚上墙角旮旯要放些好吃的,以备老鼠娶亲用,但不要有响动,要轻轻地放。干娘一再告诫我:心诚,静静地等。半夜三更子时里能听到鼠们的欢闹声,鼓声,唢呐声,-----。每每我按干娘的吩咐放好食,(连那一年到头难见的糖块都献上了),静静地躺在被窝里,想着那一群穿着小花衣,拖着长长的尾巴,有抬轿的,有打鼓的,有吹喇叭的,----那娇小的老鼠新娘,头戴艳花,浓扑胭脂,头探轿外,一脸的美滋滋。-----小小的迎亲队伍,吹吹打打,欢欢乐乐,那是何等的有趣啊!可往往是在静寂的等待中,我早已睡去。年年盼企,年年又在失望中度过这正月初十的夜。
我也心痛干娘。每当家里做点好吃的,我总吵着抢着要先给干娘送去,有时连那刚出锅馇的小豆腐,我也要抢着送去:满碗带汁,冒着热气,用布包好,麻溜地送去。干娘每当这时好说:“哎呀!俺的儿来!”
后来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,干娘一家搬走了。那是因为她的儿子转业分了工作。再后来听说。干娘60年困难时期不堪吃苞米骨子,榆树皮一类的代食品饿死了。
如今年过古稀的我喜欢冲一杯清茶,一边品着,一边回忆那些尚能记得的往事,慢慢咀嚼那些已逝的东西,虽多叹红尘万丈,世态炎凉,但也不泛有温馨久远,慈爱绵绵。我对干娘孙老太太的回忆是后者,而不是前者。

临江融媒
编辑:王丹
责编:李鸣
审核:李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