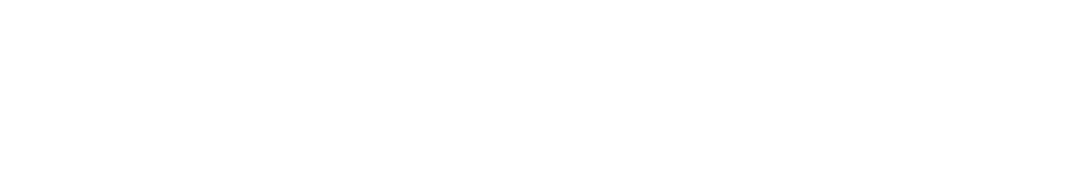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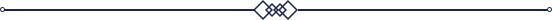


小时候,我家住在小镇大庙坎下。
据讲大庙为1913年所建。其主要是为迎合妇女求子心切的心理,募款建的送子娘娘庙。大殿内塑一位漂亮的仙女,飘飘欲动,怀抱一个孩子,意在给你送子。那年月此庙已很具规模,是长白、靖宇、抚松、临江一带最大的庙宇,人们称之为大庙,又称娘娘庙。我记事时,大庙已破烂不堪,各路神仙和那送子的美貌娘娘的塑像早已没了踪影。但随时间的推移,大庙已逐步演绎成为小镇的一个地域名,至今仍常常被人记起说起,特别是老年人往往好说:“我家过去住在大庙坎下!”,“我家住大庙坎上!”,“我家住大庙西靠窑子街那……”
(一)
大庙留在我心目中最深的印象是那里曾有棵古老的榆树,相传已活了200多年了,几抱粗,老干桠枝卓立,皮多脱落,枝已枯荣参半,高十余丈,最上的绿叶尚可蔽日。不过那树下我从没见过纳凉的人或嬉戏玩耍的孩子。倒是常见当地谁家若是死了人,在早、午、夕三个时辰群跪哭号于树下,并以汤灌地,叫“送浆水”或“送汤”。那些人往往男前女后,男多以半幅白布缠头,女多以半幅白布覆头,折叠三角(俗称“搭头”),俱都以麻绳束腰,场面让孩子们感到害怕,往往都远远地躲着。
日常就是没有这样的场景,但由于曾见过,心中打下了烙印,故每每走到这古老的树下,都是心怀忐忑,急急地走过。如果不巧碰上阴雨打雷闪电,或是青天白日落在树上的乌鸦鸣叫几声,也觉瘆人,则撒腿就跑。可我又常常从这里走,这是为什么呢?原因是我的几位哥哥好看武打小说,我也喜欢他们讲给我听,也爱看那些书中的插图,这样跑腿换书的差事就落在了我的头上。从我家出来经过大榆树下有一条纵向的路,一人宽不长,弯弯曲曲。两边房子灰白的墙上,不断出现写有大大的、蓝色的“仁丹”二字,瘆瘆然。到现在我也只知道这仁丹好像是一种药,仍不知有何功效,为何选这样僻静的地方做广告。
一出去道东拐头就到了小租书铺。小铺“门脸”也就一人宽,门是“铡板”的,即一块块竖版,白天一块块拿下来,晚上沿框槽一块块拼上,框槽上深下浅,安全可靠,堪比现今的钢制卷帘门。这书铺是老两口子开的,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。每每我去换书多数是看到那老头在哈酒(临江土语喝酒),一个小瓷碗,一双筷,一小碟虾酱。这老头喝一口酒,用筷子沾一下虾酱,放到嘴里抿一下,津津有味,旁边还放一册书,偶尔看上几眼。也许是我听的武侠故事多的缘故,有时竟幻觉这老者莫不是藏而不露的武林高手?也或是身负通天大案的江洋巨盗?而不敢正视于他。至今记忆犹新的是,租的那书多数是线装的黄色纸,书中插图多,价格也不贵,只是每册书很薄,不经看,害得我经常往返。
(二)
大庙的西北角紧挨着是小镇有名的“窑子街”,仅一小路之隔。家人说这里是最埋汰的地方,不准去玩。可孩子们的好奇心强,往往越不让去的地方越去。窑子街是几排横向小胡同,黑砖小瓦房比邻,都是平房,不像旧年间北京大栅栏的“窑子街”陕西巷都是二层楼居多。道窄两人宽的路,幽静无声。绝没见过涂胭抹脂,俏声浪语的女人,倒显得那里一切仿佛都在“睡”或“睡”去。儿时顽皮,我曾是这一带的孩子王,白天黑夜整天领着一帮孩子玩,有时还打群架。个个小胡同的墙上,那些用滑石(一种能在地上墙上划字的白石头)大书:“XXX小王八,XXX爸爸大王八,XXX爷爷老王八;XXX大坏蛋,XXX爸妈爷奶都是大坏蛋!”有时画只形象的王八,上面再写上被骂孩子的小名,这都是我们这帮孩子的杰作!有时和一二死党预先谋好,单选黑天时刻,常将邻里孩童(其中女孩为多)诓到这里,突然一人高叫:“来鬼了!”并抢先往外跑,那些跑得慢的孩子惊得哭叫连天。我们不觉得坏反而倍觉好玩。结果可想而知,第二天人家家长领着孩子找上门告状,挨骂但不挨打,原因是我在家排行最小,娘疼我,不好听的话叫“护犊子”。
窑子街第一排胡同把头那里有一位绰号叫“小油篓”的女人家,街坊辈我叫她姨娘,和我家关系好,我常去。油篓是个啥样呢?我从未见过,说是和酒篓相似,我见过旧时的酒篓。那是用刮了皮的柳条编后,再用多层的毛纸糊,用猪血澥过,是圆形轻而不透酒的一种盛器。“小油篓”可能就是人们形容她矮小粗胖而又生活无忧的一种调侃吧? 实际真的是这样的。这女人浓眉大眼,快乐的嘴唇总也合不上。印象里她的头发乌黑,“淋”满了头油,香得令人头晕,光得照人,滑得很!形象地说,蚊子落上都能跌个跟头!再就是她的臀较别的女人肥大的多,走起路来或是转转身子仿佛是一个圆的球在滚动。她基本上只一个人住,她家那位叔我只能在夏日见到。她家屋小,院子也小,独门独院。腚大点的院子里种了些花草,有“步步登高”、“鸡冠子”等一些常见的花,可也惹人喜爱!小孩贪吃,我记忆中她家从不断糖果、葵花籽一类的东西。她常常不是给我一块糖就是一把葵花籽。吃零食这可能与她年轻时的生活有关,我大一点的时候才知道“小油篓”年轻时做过窑姐。那年月俺这地方,逛窑子的男人进得屋来,一般先要与窑姐见见面,看看人,一边吃着糖果嗑着瓜子喝着茶水,一边唠嗑谈价,这糖果茶水钱往往或多或少都由嫖客拿,行话叫开盘费。故久而久之,一般的窑姐都有“嘎(读去声)嗒牙”爱吃零嘴的习惯。
然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,在“小油篓”家吃过一次蒸面饺,可香来,至今想起来还馋得慌!带了几个回家,娘说:馅是灰菜的,说吃了这东西易肿脸。脸倒没肿,可在此后生活的几十年中,我碰到这种野菜,常告诉人家,这东西能包馅吃,可至今没一个人相信。
再就是她家那位我不常见的叔叔,每当他背个包袱出门时,见过“小油篓”敞着怀,微露着那粉红色的奶绷子,把前胸箍得紧紧的,那一排排的小布扣几乎勒到白白的肉里。趿拉一双绣花鞋,急急地撵出来,这时的“小油篓”不是“挥泪而别”,只是好抻个脖子喊:“你个不死的,早点回来!听见嘛,早点回来啊!”也不怕邻里听见,一直喊到拐弯不见人影!俺娘说:她“靠”的这个人是个山里的“木把”,多数要在山里干一冬天的活,只有夏天才回来!
(三)
大庙的东北角是我大爷家(对过街就是“宴宾楼”就不属于大庙范围了)。开了一个浆子馆,每天早上人还真多。大爷过世早,大娘带独子过。每天早上开业时,大娘总一个人盘腿坐在外间一铺小炕上,旁边放一个小盆,里面放许多小白纸包,买完浆子的人都到她那领一包糖精,每包二三粒。大哥忙于炉前,大嫂穿梭各桌之间,擦桌、端碗、招待客人。大嫂长得俊俏,只是身体较瘦。人勤快,整日地忙,仿佛她有永远忙不完的事,过不完的日子,挣不够的钱!
可有一年出了大事。大嫂喝药自杀了。那年月没有耗子药,各类农药,她喝的是卤水,那是家里做豆腐用的。大嫂娘家是大沟里长尾巴岗人,长尾巴岗是临江东面过了三道沟门(现今的临城乡)的一个美丽的小山村,大嫂曾带我去过多次。那里有成片的水田,夏日最好,白天小路边的野草,稻田里成片的青苗,远方葱绿的山林,以及夜晚那阵阵不断的蛙声,都是迷人的。那年大嫂死时正值冬日,其娘家的父母亲属,七大姑八大姨,分乘了好几辆爬犁进了县城。男戴狗皮、狐狸皮帽子,女的黑布包头,均穿扎裤腿的肥大棉裤,靰鞡鞋走起路来,嘎吱嘎吱的。大闹了一场,房屋上面都给压了黄烧纸。后来以大哥戴孝,赔了一定数量的钱财才告终。从那以后,大爷家的家境一蹶不振,真正成了城市贫民。
大庙坎下我家对面临街的一趟房(里面就是窑子街小胡同) 开木匠铺的居多:有老兰家的、老孟家的、 老刘家的,基本上都是里做木匠(木匠分里做和外做,里做多承揽家具等,外做承揽造房子砍架子等,木匠的祖师爷鲁班就是外做木匠)。
但有一家是开旅店的,人称辛家小楼。二层楼,上楼的梯子是木头的,后院大且有一排平房(住家属的)。主人是供职临江林业局一位有名望的土木建筑工程师,我和他的小儿子同龄同学,儿时常到他家玩耍。见过他家的大人在二楼玩麻将牌,算账用的都是古代的铜大钱和精致的赭石色的小竹棍,寸长左右。但这位主人故去较早,印象最深的是出殡的场面:临江林业局还出了乐队,我第一次看到那背在背上的大铜号,和听到那大大的号筒发出的“嘟!嘟!嘟!”的低炮声。那时孩子们小不懂事,不懂得悲哀倒有些:“亲戚或余悲,他人亦已歌。”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跑,而倍觉好玩有趣。
大庙坎上我家东面隔两家,有一条坐北朝南的陡直小胡同,一人宽,通到下面就是泡子沿了(泡子沿再往南就是小镇有名的南围子了)。泡子沿是个脏乱差的地方,宽大而深的水沟,那水污浑不时地散发臭味,有如当年老舍笔下北京的龙须沟!家里大人也常常吓唬我们,说那里淹死过小孩。我们这帮孩子一般不过去,只有当雨季鸭绿江涨水这里的水清些才去,能捉到各类小鱼儿,人们说这时的这股水是由河东夹信子过来的故清且有鱼。只是那鱼难捉且小的可怜,好在就是玩,养在瓶子里往往第二天就“翻白肚”,都死掉了。
记忆中的大庙早没了,见过的古老榆树和那周边的人家也成了追忆,代之的是一片钢筋水泥的高楼!“大庙记事”并没有奇异动人的故事,只是儿时记得的那些普通人家的生活,普通人的事。然而不知怎的确让我不能忘却!每当回忆起来,就倍感亲切,留恋之情油然而生。当年生于斯,长于斯的大庙人啊,您们如今都在哪里?不知能否如同我一样还有点点的记忆?嗨!有与没有又能如何?我想也许那就是一场梦境,我们都曾做过,然而又逝去了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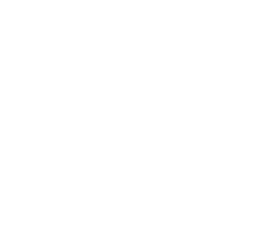


临江融媒
作者:于树刚
编辑:王英茹
责编:李鸣
审核:李伟
